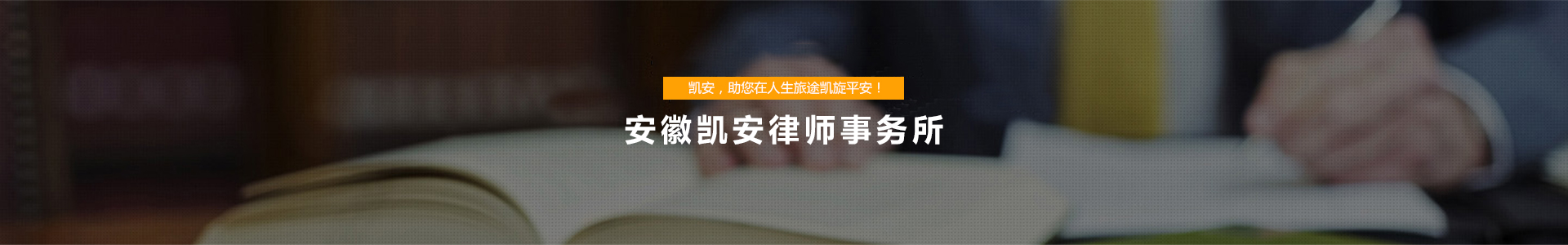安徽凯安律师事务所 朱波
[摘要]:释明权是大陆法系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
法律制度,对于诉讼的顺利进行和当事人的权利保护等都具有重要作用。当前,释明权制度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状况与民事
审判改革的发展要求不相适应。有鉴于此,本文以外国法中的释明权为参照和比较,对我国应否规定这一制度作出分析。
[关键词]:释明权 职权主义 当事人主义 制度建设
释明权是大陆法民事诉讼的概念,是指在当事人的主张不明确、有矛盾,或者不清楚、不充分,而当事人认为自己提出的证据已经足够时,法官依据职权向当事人提出关于事实及法律上的质问或指示,让当事人排除有矛盾的主张,澄清不清楚的主张,补充不充分的证据的权能。释明权一词纯粹是个舶来品,一般来说,实行职权主义诉讼体制的国家的学者对其并不感兴趣。因为在实行职权主义诉讼体制的国家,法院处于诉讼的主导地位,有着充分的诉讼指挥权。在职权主义的诉讼理念看来,法院对当事人的发问是理所当然,是自明之理。但随着我国民事诉讼制度改革,民事审判方式变革以及诉讼模式的转型的深入,“释明权”这一概念也被引入,并为一些学者所重视,关于释明权的争论也日益增多。笔者拟在本文中以外国法中的释明权为参照和比较,对我国应否规定这一制度作出分析。
一、各国概况
释明(Aufklaerung)一词原意是指使不明确的事项变得明确。而外国法中的释明,则是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是大陆法系中的概念。外国法中释明的涵义包括:(1)使不明确的事项变得明确;(2)当事人的声明和陈述不充分时,使当事人的声明和陈述变得充分;(3)当事人的声明和陈述不适当时,法院促使当事人作适当的声明和陈述;(4)促使当事人提出证据。简而言之,释明权则是为法院享有的,具有上述四项内容的职权,属于法院诉讼指挥权的一种。
① 由于“释明”纯粹是个舶来品,故我们要研究它,必须首先参阅外国法中的相关规定。
1、德国法之规定
德国是最早对释明权作出规定的国家。1877年《德国民事诉讼法》中就规定了“释明”的内容。当时对于释明是法院的一种权利,还是法院的一种义务尚存在争议。
现行《德国民事诉讼法》第139条第1项规定:“审判长应当命令当事人对全部重要事实作充分且适当的陈述。关于事实的陈述不充分的,法院应当命令当事人作补充陈述,声明证据。审判长为了到达此项目的,在必要限度内,与当事人就事实及争执的关系进行讨论,并且应当向当事人发问。”第2项规定:“审判长应当依职权,要求当事人对应当斟酌的,并尚有疑问的事项加以注意。”
②从现行的德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可以看出:德国法中释明权的范围是:(1)当事人对事实的陈述不充分时,法院应命令当事人补充陈述;(2)促使当事人声明证据;(3)审判长有疑问的事项,要求当事人加以注意。释明的行使方法,则有讨论、发问和晓谕三种。另从法律规定看,“应当”、“命令”等词语的使用似乎可以说明释明是法院的一种职权,而在德国关于释明的性质究竟是权利还是义务已无争议,即释明既是法院的一项权利,同时又是一项义务。从法院的职权看,释明是法院的一种权利——释明权(Aufklaerungsrecht),从法院的义务看,又是法院的一种义务——释明义务(Aufklaerungspflicht)。在德国民事诉讼法制度中,法院未使当事人的陈述明确,即作出判决的,当事人可以法院没有行使释明权提起上诉,请求撤消原判。当事人享有上诉权,这也说明了在此情况,释明是法院的一种义务。对于诉讼中当事人的不当声明,法院可以行使释明权将其消除,但一般认为此种情况,释明权为法院的一项权利,即使不行使释明权,也不构成违反释明义务,当事人不得将此作为上诉的理由。当诉讼中当事人的诉讼资料不充分时,法院通过释明令其补充,但该释明的行使仍然限制在当事人所提出的攻击或防御方法之中,而不能在此之外要求当事人提出诉讼资料,这也符合辩论主义的要求,此种场合的释明属于法院的一种义务,法院未释明的,构成当事人上诉理由。
2、日本法之规定
1890年民事诉讼法与德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相同。1926年日本对民事诉讼法进行了大修改。关于释明权,法律规定为可以向当事人发问。
现行《日本民事诉讼法》第149条对释明权作了规定,第一款:“审判长为了明了诉讼关系,在口头辩论的期日或者期日之外,就有关事实上及法律上的事项对当事人进行发问,并且催促其进行证明。”第二款:“陪席法官向审判长报告后,可以进行本条前款所规定的处置。”第三款:“当事人在口头辩论的期日或者期日之外,可以请求审判长进行必要的发问。”第四款:“如果审判长或陪席法官在口头辩论的期日之外,依照本条第一款或第二款规定,对攻击和防御方法进行产生重要变更的处置时,应当将其内容通知对方当事人。”
①日本民事诉讼法将释明视为一种权利。日本最高法院对释明权就采取消极态度,当事人以法院未行使释明权为由提起第三审时,最高法院均以不符合有法令的解释将其驳回,即不以释明权的不行使作为上诉的理由。
二、释明权价值分析
民事诉讼是保护私法上的权利或者确定私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是否存在的诉讼活动,源于民事实体法中的意思自治原则,现代国家民事诉讼的基石理论是辩论主义原则和处分权原则,以充分保护当事人私法救济上的自治,给予主体充分的自由。但是实践证明,完全放任当事人进行诉讼,辩论主义绝对化的做法并不可行,有悖民事诉讼法制度的其他理念。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释明制度应运而生,在民事诉讼中,释明可以说是对辩论主义的一种限制。
② 当事人的声明不明确或有不当声明或诉讼资料不充分时,如果法官能予以释明,则诉讼很显然能更顺利地进行下去,从而使民事诉讼制度能够按照设计者预定的目的运行。当然,如果法官就此作出裁判,由于当事人的声明不明确或有不当声明或诉讼资料不充分,也可能迅速结案,即判决该方当事人败诉。我们不可能要求每个当事人都是法律专家,都熟稔法律,特别是在没有律师代理的诉讼中,让当事人承担声明不明确或有不当声明或诉讼资料不充分的诉讼上的后果——败诉,这样的裁判显然是有违实体公正的。表面上的程序公正也必将带来更大的不公正。并且由此还可能引发众多的后遗症,在法官作出裁判后,当事人可能发现自己要求的法律权益未能得到保护,此即违背了当事人进行民事诉讼的主观目的——解决民事纠纷。
③ 当事人则会继续找寻法律救济途径——上诉或申诉,或者其他救济途径—上访等等,不仅浪费有限的司法资源,还可能引发一系列的矛盾。
释明权的行使可能使诉讼达到公正与效率的价值。
三、释明权对我国民事诉讼法的启示
任何制度都有其理论前提,释明制度也是如此。释明制度是以当事人主义诉讼体制和模式为其理论前提,源于当事人主义的诉讼价值观。德国和日本等国家民事诉讼在诉讼程序设计上,把当事人对诉讼实体内容有权处分的当事人主义与法院对诉讼程序有权指挥的职权进行主义融合在一起,形成德国和日本等大陆法系国家特有的诉讼模式。职权主义与当事人主义并不冲突。笔者认为,当事人主义即是由当事人收集证据或进行证明,当事人主动向法院提出申请,由当事人启动程序。而职权进行主义即是当事人在法院介入和指挥下收集证据和进行举证。德国和日本等国家所采取的职权进行主义不仅不否认当事人在诉讼中起决定作用的当事人主义诉讼原则,相反法院支持和帮助当事人进行诉讼,有利于加快诉讼进程。
反观我国,民事诉讼模式大体经历了198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时期的超职权主义诉讼模式阶段,199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法院职权弱化阶段。1998年6月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民事
经济审判方式改革的若干规定》中“法院在开庭前应当告知当事人围绕自己的主张提供证据”的规定,首次确立了法官的举证释明义务。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出现了更多涉及释明权的规定,其进步性在于:一是强调法院与当事人在诉讼程序上的相互制约、相互协调、相互促进;二是不仅规定了举证释明,而且规定了澄清当事人主张的释明、以及法律观点开示等内容。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模式,虽然与试行法典相比,法院的职权有所弱化,但仍然比较广泛和强硬,笔者认为,仍属于职权主义。我国民事诉讼的现行模式并非理想定型,仍需进一步改革和完善。(由于本文主旨不在于讨论诉讼模式问题,故此处不再赘述。)德国和日本的改革模式应代表了民事诉讼改革的总趋势,值得我国借鉴。
因此可以说,在我国尚不存在释明制度生存的土壤,作为基础的理论前提尚没有建立。虽然我们正朝着这个方向努力。故在我国目前的裁判理念和诉讼模式基础上,谈论应否引入释明权是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因为从我国民事诉讼一般理论来看,法院的释明权是完全没有必要的。现阶段我国法院的职权仍然比较广泛,主要表现在:(1)法院有职权启动某些诉讼程序;(2)法院具有查证的职权,所查证据可作为定案依据;(3)辩论主义未作规定,当事人的处分权受“法律规定范围内”限制,为法院干预留下缺口;(4)纠问式审判方式没有根本变化。
①法官在诉讼中仍处于主导地位,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法官的发问、提示也不无合理。在这样的理论背景下,制定释明权,只可能增添误解——我国的民事诉讼改革在走回头路。因为在现有的我国的法律文化下,是不可能理解释明权的本质内涵的。民事诉讼作为法律文化是西方的东西。
②故西方的先进理论、制度,我们都应该研究、学习。但我们在引入外国的法律制度时,不应仅关注这一制度可能会解决我国民事诉讼改革中存在的某个问题,就制度论制度,而应更多的关注这一制度的历史沿革、渊源,其背后的理论前提,承载它的法律文化。正如有学者指出,目前我们对我国民事诉讼审判方式改革的认识还很肤浅,只限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浅层次水平。
③ 笔者认为,我国的民事诉讼改革应改革根本的诉讼机制,改革也是革命,而不是“作秀”,仅仅关注公开的、表面的制度设计、权利配置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相反,可能将改革引上邪路。
1、 张卫平:《诉讼构架与程式——民事诉讼的法理分析》,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184页。
2、 参见张卫平:《诉讼构架与程式——民事诉讼的法理分析》,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187页。
3、 白绿铉编译:《日本新民事诉讼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71页。
4、关于释明权与辩论主义的关系大体有两种观点:一种为限制说,一种为补充说。笔者倾向于限制说。参见张卫平:《诉讼构架与程式——民事诉讼的法理分析》,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190页。
5、 当事人在选择诉讼这种方式作为其救济途径时,他的主观目的就是要解决他当前面临的纠纷,很难想象他会去关心法律如何创制,创制者创制过程中有如何的考量、取舍、价值分析等等。笔者认为民事诉讼的目的应采多元说。参见陈桂明:《程序理念与程序规则》,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113页。
6、参见陈桂明:《诉讼公正与程序保障》,中国法制出版社,1996年版,182、183页。
7、《三月章先生回答关于新民事诉讼法制定的提问》,日本《法学家》杂志第1098期,1996年10月1日。转引自白绿铉编译:《日本新民事诉讼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31页。
8、白绿铉编译:《日本新民事诉讼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29页。